谢其:坏景致
2019-09-25 15:35
前言
对谢其来说绘画是一直钟爱的方式,她喜欢这种规则简单,变数复杂的游戏,甚至目前的个展她也私自认为是一次对绘画的礼赞。
她的创作思路实际上是一脉相承,要塑造的,是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新作中出现了大量的“毛”和“钱”的元素,其实跟政治和经济学并不关系,只是一种“用普通材料做大餐”的思路导致。
在著名艺术家何云昌看来:“谢其的作品透露出浓郁的悲凉气息。“紫的隐退”似乎传达了整个民族的悲哀、伤痛和希冀;“钱币系列”延伸了物我两忘的忧郁情怀。当一个艺术家倾心倾力呈现的并不止于狭隘自我感慨的时候,他的心随世事万物跳动。
当一个艺术家倾心倾力呈现的并不止于狭隘自我感慨的时候,他的心随世事万物跳动。比如未未,也曾提着身家,以艺术的方式奔走呼号,而不是为一己之欲,念。当他专注于艺术领域时,世奉其为佼佼奇才,当他以艺术介入众生,就得面对、承受和担当……世奉之为神。像一滴水一样融入大海,也可以堪称伟大。”
墙报专访谢其:我要塑造的,是“熟悉的陌生人”
导读:谢其说她的创作思路实际上是一脉相承,要塑造的,是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新作中出现了大量的“毛”和“钱”的元素,其实跟政治和经济学并不关系,只是一种“用普通材料做大餐”的思路导致。真正的兴趣点在于:脆弱、权利的脆弱,力量的被消解,被时间,空间,甚至只是被华丽的图案和浓重的颜色所消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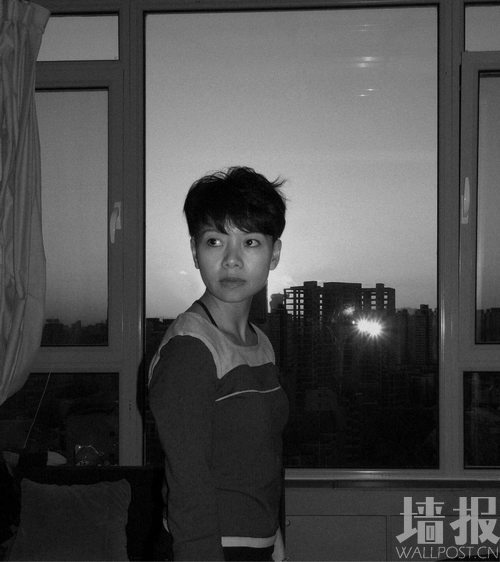
谢其
你的作品里出现很多“钱”和“毛”的元素,是怎么考虑的?可以谈谈你主要的创作思路吗?感兴趣的题材主要是?整个创作有没有线索可寻?
早期作品如个展《午后》,是关于父母;在个展《单挑》里,也有父母,还有亲近的朋友如《Madame Fan》里的樊其辉,还有一组是关于附近天桥的一个乞丐。题材是切肤的,表达的体验也是个人的。这次展览里的系列,选择了具有普遍性的符号,“毛”“钞票”,都是不需做特意说明的题材,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相关体验。此类题材已经熟烂到人们不屑去触碰的地步,但我的作品又与普遍的情感关系不大,依然是个人表达,思路实际上是一脉相承,我要塑造的,是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政治和经济学都不是我能讨论的;脆弱,权利的脆弱,力量的被消解,被时间、空间,甚至只是被华丽的图案和浓重的颜色所消解,这些才一直是兴趣所在。
还是用普通材料做大餐的思路。

午後-01
最新个展和以前的作品虽然绘画技巧的表达一脉相承,但关注方向和表达观念都完全不同,能谈谈这期间的变化吗?展览结束后,有下一阶段的创作方向吗?同一主题的创作会再延续吗?
钞票的作品还有一点要完成,正在进行的一个系列叫“坏人和洋人”,是一个肖像系列,引用了两个最脸谱化的词汇,选择的是具有复杂气质的人物,目前有西克(Uli Sigg)和老艾,接下来还有其他人,跟艺术有关或无关的……我以前有一个题材是“性”,还在延续,也许在表面形态有一些变化,但还是忧虑的性和欲望。
多以绘画为主要创作形式,怎么看待艺术媒介选择?会有其他尝试吗?
绘画是一直钟爱的方式,我喜欢这种规则简单,变数复杂的游戏,甚至目前的个展我私自认为是一次对绘画的礼赞。我当然不反对别的形式,上次展览做过跟那组绘画有关系的雕塑,去年也跟一个乐队“大忘杠”合作,设计制作了舞台,这个经历非常棒,有条件还会继续。但不管做什么我得做自己能掌控的东西,要参与大部分工作,因为我还是手工艺爱好者。
绘画要干的活还真的很多,没干完呢!

《麦克风》-2010年
你的作品带有一种宏大的悲凉感,是这样吗?这也是极少在女性艺术家身上看到的。你会从男性角度去认知这个世界吗?怎么看待女性意识?
我不太清楚所谓男性角度是什么,我了解的都是个体。如果以普遍标准和既定特征去分辨男女的话,我认为每个人都至少是双性人,有的含99%男性,有的含30%男性,有的0.5%......再阴柔的人都会在某些特定时候显示出阳性气质来。所谓“悲凉”,我理解为一种类似冷棉被的质地,在女性艺术家那里得到的体现也是明显的,比如我非常喜欢的Billie Holiday,或者Pina、 Louise Bourgeois。
截止目前为止,有没有经历过重要转折?如果遇到困境,采取什么方法突破?
死亡、离别、失落,生活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情节剧。困境无所不在,基本上是已经构成生活的砖瓦墙壁,我已经习惯在里面做白日梦。而绘画的困境,我相信只要还有颜料,总能帮助我到达另外一关。
你觉得和同龄艺术家相比,有什么相同之处?而你的作品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气质的?
关于同龄人,你可以从生物学或社会学上去分析,身体、经历带给艺术的推动或者束缚等等,我真的不擅长这样的宏观统计,而更在意个体差别。从心理上来讲我没有同龄人,或是年迈的儿童,或是幼稚的老人,或是在青春的焦灼幻象里。
封闭是优点吗?
“这是谢其的目光,注视着你我。”想说的,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关系?
我是对观众有一点奢望,希望能赚取他们的时间和耐心,还有理解力。所谓“谢其的目光”我认为是近距离的,亲密的而同时是疏远的,近距离的虚焦带来识别的难度,愿意参与这个游戏的人也许会找到一些乐趣。有辨识难度的作品会自己挑选观众,当然观众也可以不接受附加条件直接怕死掉它们。

女王高跟鞋
如何面对作品收藏?作为艺术家,会比较期望怎么的艺术市场环境?
这么多年当中,碰上的真正的阅读者不多,但他们都有较深入的理解,甚至在积极传播,很令人鼓舞。我当然希望藏家们也是真正的阅读者,我无法许诺升值,只能许诺一些阅读的快感。一厢情愿的期待更多藏家。
何云昌:怀风抱露——谢其新作展有感
导读:谢其的作品透露出浓郁的悲凉气息。《紫的隐退》似乎传达了整个民族的悲哀、伤痛和希冀;“钱币系列”延伸了物我两忘的忧郁情怀。当一个艺术家倾心倾力呈现的并不止于狭隘自我感慨的时候,他的心随世事万物跳动。

何云昌
(作者:何云昌)
谢其的作品透露出浓郁的悲凉气息。《紫的隐退》似乎传达了整个民族的悲哀、伤痛和希冀。那种悲天悯人的气息甚至掩盖、超越了谢其精湛、酣畅淋漓的技艺,弥漫渗透在空间和心胸,而图像以及图像附着的愉悦也淡然渐逝,悲欣气息扑面而来。

紫的隐退
“钱币系列”延伸了物我两忘的忧郁情怀。风景和钱币的经典图像重叠、掩映、混合,致使幼稚阅读图像为乐事的俗趣荡然无存,似曾相识的物象,似是而非的迷离,如果不经提醒,那张布达拉宫的伍拾元纸币的作品,差点误以为是幽灵和异域。迷蒙、妖冶而又亮丽的景象,婉约、哀怨、层层叠叠。画面已令人动容,透过那些作品又能呈现怎样的伤痛,悲哀和苍凉无奈呢……

即使倒退到血腥的春秋战国,治世仍然秉持“四海之内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的宽容气质,俯仰令人扼腕,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国吗?这都什么时代了?什么时候我心才不忧伤?

当一个艺术家倾心倾力呈现的并不止于狭隘自我感慨的时候,他的心随世事万物跳动。比如未未,也曾提着身家,以艺术的方式奔走呼号,而不是为一己之欲,念。当他专注于艺术领域时,世奉其为佼佼奇才,当他以艺术介入众生,就得面对、承受和担当……世奉之为神。像一滴水一样融入大海,也可以堪称伟大。

